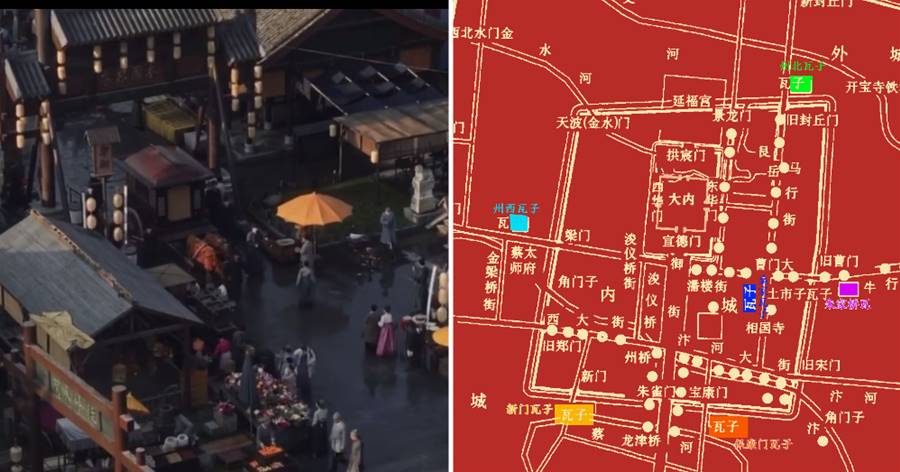孔子作為一代圣賢,在春秋這樣特殊的時期迅速成熟,結合周代的禮樂制度,順利構建了屬于一套完善的思想體系,影響深遠。
而他的思想體系的建構, 是以天下歸仁作為自己的最終目標, 且為了實現這樣的目標即便犧牲再多也在所不惜。
這樣一種將自身的理想與社會的理想相互結合的指引之下,孔子一直將仁貫穿到具體的實踐中去,甚至是自己的整個人生。

因材施教等觀點的提出,是那個時代無數不多的閃耀思想,在這其中體現了對每一個個體的多樣與尊重,其中對每個學者自身獨特的特點與個性給予了充分的肯定。
孔子獨特的思想特別是在道德思想與教育觀點上,指出知行合一以及身體力行,哪怕到現代也依舊有著十足的參考意義。

有很多人好奇,被稱為圣人的孔子,如果把他的成就放到現代,他的文化水平能不能達到現代社會研究者的水準?
在他看來,志向在道德的教育中高于一切,而其中志之最高者當以仁為核心,對于仁的追求與實現,并作為自身的遠大理想,從而實現最終的天下歸仁的大同社會無疑是至善之為。

要實現求仁、得仁的目標與理想,首先要做到的是塑造一個理想的君子形象,而這樣的君子形象首先應當做到成為道德的典范所在,并引導更多社會成員向著這樣的典范靠近。
而這樣的君子常常具備著溫文爾雅以及堅韌自強等諸多優良的品質,所謂小人無仁,而君子自當以德立身,知仁、行仁甚至殺身而成仁。
君子不應當為了世俗的貪欲而忘卻仁的本質,做出違背仁的原則,甚至在生命與仁德沖突之時,應當舍棄生命來實現仁德。

孔子自身所建構的思想道德體系中,從修養水平進行劃分可分成至高至善的圣賢,再到孜孜不倦的君子,接著才是普通人以及小人。
君子將仁德作為自己的最終目標并不斷追求,有著相對高的道德修養水平以及道德的自覺性,可謂是道德風尚的中堅力量,而小人則是無任何道德自覺性,甚至破壞以及踐踏道德,而普通人則是介于二者之中。
在孔子的道德體系之中,圣人境界是算得上是一種超人,是集眾美一身的最高典范,圣人的境界非常難以達到,哪怕是堯舜禹也成為不了孔子心目中的圣人形象。

圣人的境界在于憑借自身的博學以及極高的修養而惠及大眾,為天下人謀取福利,出于仁但是又超越了仁。
孔子的突出貢獻在于為讀書人甚至是普羅大眾樹立了一個能夠達到的目標,即一個理想的君子形象,同樣也設置了一個至極的圣人目標,希望君者能夠達到圣人的境界,而不斷進取。
君子形象的設立不僅將讀書人的道德以及思想進行了規范,同樣也對治理國家的統治者乃至皇室貴胄都需要遵循著這樣一套傳統的道德規范。

在《論語》中孔子對統治者對于選舉人才提出了自己的建議與看法,同時又勸勉這些擁有著俸祿的君子不要因為五斗米而折腰,要秉持著追求仁義道德的最終目標。
孔子的突出貢獻在于,對君子與小人從傳統社會中等級觀念中解放出來,而走向了精神與人文上的高低作為評價個人的標準。
這種標準的確立,使得任何階級都必須同將提高自身修養為根本要素,同時將道德與政治相結合使得上行下效,最終達到一個天下歸仁、天下大同的終極盛世之中。

為政以德的確立,不僅僅是孔子的在政治與道德的主張,而且成為了中華上千年的封建傳統的根基,深深嵌入在每一個中華民族的人民的基因之中。
盡管隨著社會的不斷變革,儒家思想也再不斷發生著變化與革新,但本質上對于仁德的推行依舊是每一個朝代對于儒家的信奉。
孔子希望建立起一個天下歸仁的道德教育體系,為了實現這樣一個在社會上充斥著仁義道德的社會,在政治上施行著仁政的極度理想的終極目標。

他首先從個體出發并逐漸推及到社會,首先要實現人人將仁德作為自己的根本志向,并堅持貫徹,當這種竭盡所能只為成仁的社會成為了全體的共同意識之后,社會矛盾自然而然也會隨著瓦解,同時社會秩序也自然會恢復穩定而實現天下歸仁。
孔子為了實現天下歸仁的目標,他首先將目光放在了個體之中,如何由一人而推至眾人,人人都能做到克己復禮那麼天下歸仁便有望實現。
然而天下歸仁的目標在孔子的闡釋中似乎顯得比較簡單,然而本身人作為一個十分獨立的個體,并不是人人都能夠做到摒棄自身私心而在待人待事上做到不分彼此。

這種極高的道德修養不但需要著長期且廣泛的思想道德教育,同時也需要著統治者以身作則不斷推行,做到仁政仁德,親民若子。
無論是個體還是作為執政者,這樣終極的目標實際上很難最終實現的,哪怕是孔子一生不斷推廣與實踐,也不得不道出一聲,吾道不行矣的悲慨。
然而正是這種明知不可為而為之,哪怕是知道這種大同社會的實現在當下很難做到,但也依舊是堅持自己的理論體系,并堅持貫徹到底,這樣走在時代前列,如此成熟的思想也依舊值得人們重視與尊重。
仁在論語之中出現的頻率十分之高,甚至可以說貫徹著孔子整個思想體系的核心,孔子從仁的角度出發構建了一套完善的道德范疇,對于仁的解釋,他在結合不同的條件、不同的環境給出了獨特答案。

從各個角度對仁進行了定義,反而呈現除了仁的定義本質上并不是絕對化,而是一種大道至簡,是一種無形的至道。
孔子認為仁作為一個總綱,是所有道德的核心與基本原則,而至于孝悌忠信只是仁在各自領域中一個具象化的體現,但都貫穿著仁的思想精華,是仁者愛人在不同層面上的不同體現與具象化。
這種具有超越性的、抽象性且兼具普遍性的仁,雖然無法被固定下來,被給予一種確切的定義,但都表現出一種共性,那便是愛人的共性。

愛人精神作為仁的靈魂與關鍵的內核是人的根本屬性,仁者愛人是一種人與人之間相親相愛的表現,一種是基于血緣關系而產生了自然的親屬關懷。
這種自然的親屬關懷中孔子又指出,孝悌之愛即對父母、兄姐弟妹的愛應當是仁之本位,而第二種將自然之愛擴大化,成為了一種普遍性的博愛,則在孔子的理解中更多是呈現出一種忠與恕的仁道。這便是孔子在仁的教育上予中華的突出貢獻。
義同樣是孔子道德體系建設中的一個重點之一,常常作為一個價值與行為的標準與判斷的準則,義作為一種最為高尚的道德標準往往成為君子的特殊標簽。

君子在做人行事上更多需要參考的同樣是能不能達到義的標準,而對于義的定義與界定,孔子認為義不單單是體現在人際的交往之中,同樣也體現在政治上,特別上在治理國家,在于對百姓的管理之上。
全社會應當以義作為最佳的標準而施行,統治者應當重視義,而百姓也同樣是重視義,如果君子有勇而失去了義,那麼這樣的人也只會動亂,而小人在行事上有勇而沒有義,則走入盜寇之流。
與仁和義不同但有聯系的是禮,禮作為仁義在具體的實踐上的一個非常顯著且關鍵的載體,在論語之中展現得淋漓盡致。

克己復禮作為孔子理論體系的關鍵思想之一,在對于仁義道德、仁政的追求上,特別上在建立一個良好的社會秩序上,孔子認為禮是脫不開關系,是仁義在現實世界的具體與外在表現形式,往往是實踐也是實現仁義的必要手段。
孔子的禮是基于堯舜禹時代,并從周禮之中借鑒而出,為的是從這個禮樂崩壞的時代之中得到撥亂反正,他強調宗法中在登記上長幼有序,禮對于人際關系以及社會秩序的維護與穩定甚至是對個人的道德意識的培養有著關鍵的作用。

盡管孔子借鑒的是周禮,然后他卻超越了周禮之中對于封建地主以及政治規范的維護,超越時代式的認為禮不應當只是一種形式而是一種真正的灌注著仁義思想的精神外在表現。
孔子對于周禮中蘊含著的仁義道德精神內核提取出來,并在周禮的外在儀式上得到了完善,推崇周禮、復辟周禮本質上只是為了實現天下歸仁的終極理念。
孔子本質上否定了這種浮于表面的參拜儀式,他認為最為重要的應當是周禮之中蘊含著的仁的精神內核,即他指出大禮不變而小禮變。
孔子的貢獻以及影響不應從而今時代的角度出發去看待,作為當時時代乃至后續上千年的思想最強音,也不單單只是現代代表最高知識水平的院士所能涵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