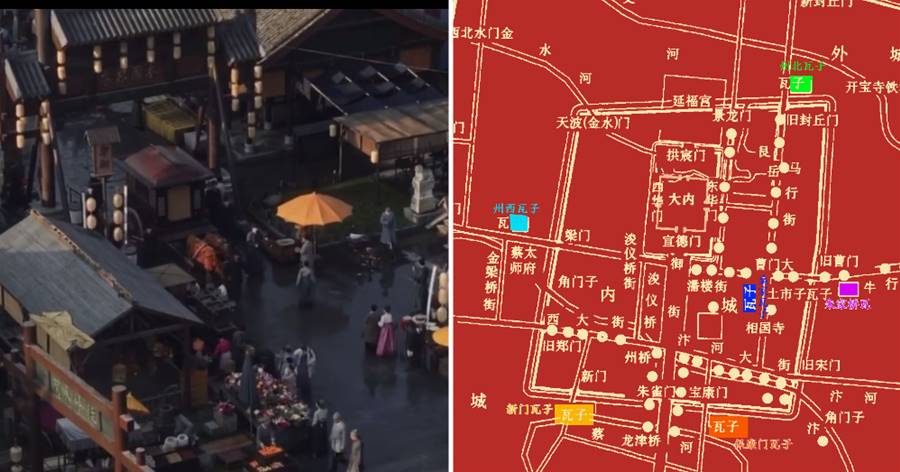在英國的大英博物館4號展廳里,收藏著一塊長方形的黑色玄武巖石碑,它頂部上有著斷裂痕跡,碑身上刻著密密麻麻的文字符號,看上去莊嚴而又神秘。

這塊石碑,就是名聞遐邇的 羅塞塔石碑,它是古埃及王國遺留下來的珍貴歷史文物,距今已經有著兩千多年的歷史,也是大英博物館的鎮館之寶之一。
羅塞塔石碑上所刻著的文字符號,是早已失傳的古埃及文字,如何破譯它,難倒了無數考古學家們。
最后,是一位潛心專研過中國文字的法國學者商博良站了出來,他從中國文字中得到啟發,最終用「漢語」的邏輯破解了這段文字。
羅塞塔石碑文字的破解,也奠定了研究古埃及語言與文化的基礎,由此更誕生了古埃及學這門歷史學科。
羅塞塔石碑雖然收藏在大英博物館,但它最早是由法國人發現的,而它的出土,和法國歷史上一位舉足輕重的大人物 拿破侖離不開關系。

1798年的6月份,正是拿破侖在歐洲暫露頭角的時候,擔任法蘭西共和國意大利方面軍總司令的他,在意大利北部擊敗了奧地利帝國后,名聲鵲起。
當時法國正與英國在中東爭奪殖民地勢力,拿破侖被派往中東,以遏制英國的擴張。
拿破侖的遠征軍首先抵達了埃及,攻占了亞歷山大城,驅逐了英國勢力,很快就基本占領了埃及全部陸地領土,進展十分順利。
年輕的拿破侖雄心勃勃,除了希望在軍事政治領域奪取更大的權力以外,他也希望在歷史文化領域建立自己的名聲,作為軍人的他,還特意為自己取得了法國國家研究院的院士身份。

這次遠征的目的地埃及,是歷史上著名的文明古國,拿破侖從法國帶來了一百多位知名學者,組建了埃及研究院,希望也能叩開埃及歷史文化研究的大門。
這次遠征也果然有了令人驚喜的收獲,在1799年的8月,拿破侖麾下的一名工程兵軍官布夏爾中尉,就在偶然之中,發現了一塊珍貴的石碑。
當時,為了防御英國軍隊的進攻,拿破侖的軍隊,正在尼羅河入海口西邊支流三角洲上的拉希德城堡附近修建工事。
布夏爾帶領著士兵和民夫們拆除了地面的房子,沿著戰線挖掘壕溝,正在忙碌之時,有下屬向他報告,發現了一塊刻滿看不懂的符號的石碑。

此時正在戰事的緊要關頭,本來這塊黑色玄武巖石碑的命運,很可能就是和普通石板一樣,成為法軍防御工事的一塊地基了,所幸它遇到了對考古略知一二的布夏爾。
布夏爾知道埃及有著淵源流傳的古代文明,這塊石碑可能大有來頭,因此趕緊報告了上司,最終,拿破侖下令把這塊石碑運往開羅。

在開羅的法國歷史學者和考古專家們,立刻被這塊石碑震住了。
只見它頂上大約有三分之一的部分已經斷裂不見,留下的部分高約1.1米,寬75厘米,厚28厘米,上面刻著的碑文分為三部分,各自是不同的文字,其中最下部的是可以辨認的古希臘文,而上面的兩種文字在當時無人知曉。
這些碑文在地底埋藏了多年,出土后依然清晰可見,而整塊石板留下的文字足有上百行,如此長篇的完整碑文在考古發現中也極為罕見。
學者們立刻意識到這塊石碑的巨大價值,有兩位專家還專門從法國巴黎趕來,用石膏把石碑上的文字復制下來,制作成拓片,方便研究。
法國在埃及發現一塊珍貴古石碑的消息也不脛而走,按考古學界的慣例,本來應該按它被發現時所在的拉希德命名,但讓人啼笑皆非的是,當時的法國士兵將拉希德誤譯成了羅塞塔。

從此這塊石碑就有了羅塞塔這個流傳至今的名字,而原來的拉希德城堡也因此被改名為羅塞塔。
隨后,法國本土發生了政局變化,急于奪權的拿破侖匆匆趕回來法國,英國趁勢打敗了留在埃及的法國軍隊,重新掌握了埃及的局勢。
在驅趕法國軍隊離開埃及時,向來喜歡搜刮各國歷史文物的英國人,要求法軍把在埃及發現的所有文物移交給英國人。
知道羅塞塔石碑價值的法國人,并不想放棄它,偷偷把它藏在一艘撤離的船只上,想要蒙混過關,把這塊珍貴的石碑運回巴黎。

已經聽到消息的英國人,也早就盯著法國人,在嚴密的檢查下,裝有羅塞塔石碑的法國船只,在起航前的最后一刻被攔截了。
英國人找出這塊石碑后,將它作為戰利品運回了英國。
從此,羅塞塔石碑就被保存在大英博物館的埃及展廳,一直展覽到今天。
得意的英國人,還特意在石碑展出時的標簽上,寫上「大不列顛軍隊征服埃及的戰利品」,炫耀著他們在埃及的勝利。

羅塞塔石碑最終花落英國,而關于上面碑文的破譯,則剛剛開始。
根據考古學家的鑒定,羅塞塔石碑有著兩千多年的歷史,而它到底屬于哪個朝代,背后又有著怎樣的故事,就要靠上面的碑文來告訴我們了。
羅塞塔石碑的碑文分為三種文字,最上面的文字是古埃及的象形文字,因為頂部已經殘破,留下來的只有14行。

而中間保留下來的完整碑文,是古埃及的另一種文字: 世俗體銘文,又被稱為埃及草書,共有32行; 底部的文字是54行的古希臘文。
三種文字之中,古埃及象形文字和草書,都已經失傳很久,當時的歷史學家們都讀不懂其中的含義,而幸運的是,歐洲學者們已經熟練掌握了古希臘文。
底部這篇完整的古希臘文,就講述了石碑的歷史由來,原來這塊石碑是在公元前196年所刻。

當時正值古埃及的 托勒密王朝,年幼的 托勒密五世即位后不久,對埃及的祭司群體十分優厚,他頒布了一系列法令,取消了神廟所欠的稅款,還撥款重修了神廟并贈送了谷物。
如此的恩典也自然得到了埃及祭司們的擁護,在公元前196年的春天,全埃及的祭司集中起來慶祝托勒密五世登基一周年,并把歌頌他的祝詞用三種文字刻在石碑上。
而在最后一句,還專門點明,將用神圣的文字(即埃及象形文字)、本國的文字(即世俗體銘文,又被稱為埃及草書)和希臘的字母把同樣的內容刻在硬石碑上。

這也為破譯石碑前面兩篇文字留下了一把鑰匙,雖然兩種文字都已失傳,但我們已經知道它們記述的內容和希臘文一致,可以通過希臘文的內容來還原翻譯。
而通過破譯石碑文字,也能幫助我們掌握埃及象形文字和埃及草書這兩門已經失傳的文字,重新解讀埃及已經沉寂泯滅兩千多年的文明。
就這樣,歐洲各國的歷史學者和考古學家們,紛紛投入到破解羅塞塔石碑文字的工作中,而法國事先將石碑上的文字制作成拓片廣泛流傳,也為破譯工作提供了便利。
首先取得一點進展的,是法國著名的 東方學家薩西,他精通中東的敘利亞語、迦勒底語、波斯語、土耳其語和眾多的古代阿拉伯語言,也被認為是破解羅塞塔石碑文字的不二人選。

薩西反復專研了第二段的世俗體銘文,覺得和自己研究的阿拉伯字母很像,因此斷定世俗體銘文有著字母的成分。
因為,他從已經知道內容的希臘碑文中,挑選了幾個特定的詞組,希望從世俗體銘文中找到相對應的單詞,以此來進行破譯。
但他的進展并不順利,除了確定了極少數的幾個稱呼名字的詞組外,比如托勒密和亞歷山大,其他的詞組依然毫無頭緒。

薩西很快就失去了興趣,但 他的學生阿克布拉德倒是又取得了一些進展。
阿克布拉德是一名瑞典的外交官,他業余跟隨薩西學習東方學,尤其對古埃及的銘文研究興趣濃厚。
從師父薩西那里拿到羅塞塔石碑銘文的他,在薩西的基礎上,又在世俗體銘文中找到了幾個能和希臘文對應上的詞組,最終確定了16個專門的單詞。
但他的研究也和師父一樣,很快就陷入了瓶頸,單純用字母比對字母的方法顯然沒辦法洞察埃及古語言背后蘊藏著的規律,沒有辦法攻克羅塞塔石碑的。
而且薩西師徒的研究,都只局限在第二部分的世俗體銘文,對于第一部分的古埃及象形文字毫無頭緒。

這時,是一位著名的物理學家,為破譯羅塞塔石碑帶來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轉機,他就是 英國的托馬斯·楊。
托馬斯·楊是我們中學物理課本上楊氏雙縫干涉實驗的發明者,他是一名興趣廣泛的學者,除了物理學以外,他在醫學、古文字學都有著精深的研究。
托馬斯·楊在1814年拿到了羅塞塔石碑的拓片,開始了他的研究,他也把物理學的嚴謹與細致用在解讀古埃及文字上。

研究時,托馬斯·楊將石碑上的三種文字分組進行對照研究,先是掌握了86個古希臘文字和埃及世俗體銘文互相對照的詞匯,進而又總結了218個世俗體銘文與200個象形文字的對應關系。
在此基礎上,他又確定了象形文字的正確閱讀順序,以及石碑銘文上人像、鳥和動物符號呈現的不同朝向特征。
1819年,托馬斯·楊將他的研究成果以論文的形式發布,被稱贊為埃及學的創世之光,洞穿了遮蓋埃及象形文字多年的黑暗。

雖然托馬斯·楊將羅塞塔石碑的解讀推進了一大步,但依然只能碎片化地解讀部分詞組,無法破譯整個古埃及語言體系,石碑上的銘文依然遮蓋在黑暗的迷霧之下。
羅塞塔石碑,最終還是等來了破譯他的真命天子,法國人商博良。

商博良出生于1790年,從小就極具語言天賦,而神奇的是,他的相貌也極具東方色彩,被人稱為宛如古埃及法老轉世。
商博良在11歲時就初通拉丁文和希臘文,1802年來到法國格勒諾布爾的學校就學,開始學習希伯來語,以及敘利亞語、阿拉伯語和迦勒底語這三種閃族語言。
也是在1802年,他結識了曾跟隨拿破侖遠征埃及的著名學者傅里葉,在傅里葉家中,他第一次見到了羅塞塔石碑的拓片。

傅里葉曾擔任埃及研究院的秘書長,長期主持埃及考古資料的整理出版,而無人能讀懂的羅塞塔石碑銘文,一直是他多年來的一塊心病。
聽說了羅塞塔石碑的由來后,年輕氣盛的商博良,發誓一定要讀懂上面的碑文。
在這之后, 為了積累語言學的基礎,商博良又刻苦攻讀了眾多東方語言,比如希伯來文、巴比倫文、波斯文、梵文、中文等,而其中的中文也成為了他後來破譯羅塞塔石碑的關鍵鑰匙。

為了破解古埃及文字,他還特意學會了埃及的一種方言科普特語,這種語言是被認為是和古埃及語言發音最為相近的一種語言。
商博良從1808年開始正式研究羅塞塔石碑上的文字,中間因為政局動蕩和個人病痛而歷經坎坷,但也終于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
這個突破,來自于他糾正了研究古埃及文字學者們的一個共同錯誤。
說到這里,就要說起表音文字和表意文字的區別了,表音文字是由純粹表示讀音的字母構成,書寫的文字不能直接對應含義,而表意文字則由表達含義的圖形演變而來,書寫的文字與讀音無關。

以往的羅塞塔石碑的研究者們,普遍認為上面的古文字是一種表意文字,與表音無關。
托馬斯·楊的研究要更進一步,認為其中有著一定的表音符號,但他也認為只有其中的外國人名才是表音的。
而偏偏是這個誤區,導致始終沒法建立古埃及語言的整個語音和語法規則。
商博良是在一次偶然的對比中,發現其中象形文字的符號數有1419個,遠遠多于希臘文單詞的486個,而如果埃及象形文字是全部表意的,一個符號代表著一個含義,那麼與希臘文單詞之間的數目應該大致是相等的。
從兩者懸殊的數字差異上,商博良推斷,埃及象形文字的字符既有表音符號,又含有表意符號或其他符號。

而這時,以往學習過漢語的經歷,幫助他更好的理解了這種獨特的結構。
漢語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語言,一開始是由圖形組成的象形符號,漸漸由圖形轉變為筆畫構成的方塊字,而在演變過程中,原來表意的象形文字逐步變成了兼具表音表意的文字,最終漢字具有了形象、聲音和含義三種結合一體的獨有結構。
而古埃及文字和漢語有著異曲同工之妙,它既不是純字母表音文字,也不是純表意文字。
它的書寫體系中,除了作為限定詞等特殊用途的符號之外,主要由兩大類符號構成,即表音符號和表意符號,這是一個復雜的,同時兼具表意和表音的文字體系。

商博良在漢語的啟發下,成為了識破古埃及文字這一結構的第一位學者。
在1822年,商博良在巴黎科學院會議上公開宣讀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引發了學界轟動,兩年后,商博良正式出版了專著 《古埃及象形文字體系摘要》,徹底破譯了羅塞塔石碑和古埃及文字體系,這本著作被稱為古埃及學的開山之作。
隨后,商博良還帶隊專程赴埃及進行考察,當地的居民爭先恐后的來看這位「看得懂古代石碑的人」。

為了紀念商博良的貢獻,他幼時所居住房屋的地面上,也刻上了羅塞塔石碑的銘文,以供游客們瞻仰。
羅塞塔石碑上文字的破譯,也幫助我們豐富了對古埃及文明的認識,這一切,也有著中國漢語的功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