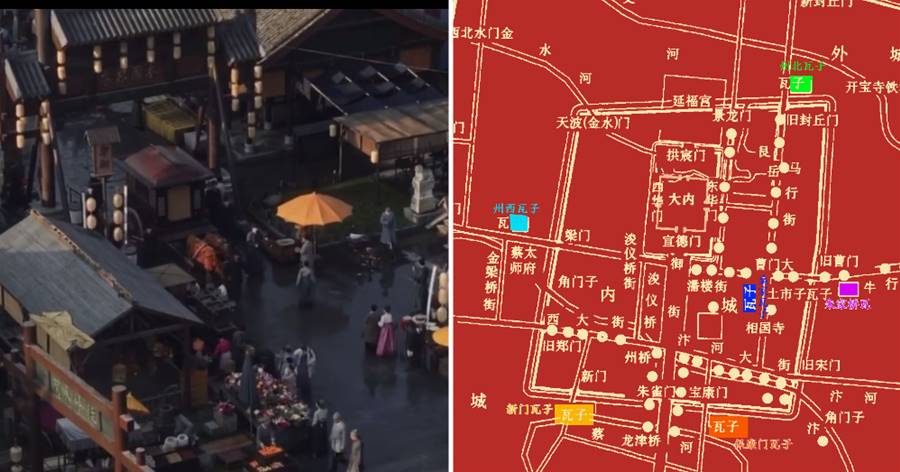隨著三星堆的持續「上新」,成都平原的考古發現再度驚艷了世界。但縈繞在人們心中的謎團卻愈加撲朔迷離。
在搞清楚這個問題之前,我先把最新的考古發掘主要成果做一個簡單梳理和解讀:

首先,三星堆目前共發掘了8個祭祀坑(準確的說法是器物坑),除了1號、2號坑是早在1986年進行了考古發掘外,另外6個坑均為2021年以來最新發現和陸續發掘的。
經碳14測定,祭祀坑測年數據在公元前1131年—公元前1012年,之所以是一個時間區間,這是受碳十四測年技術的局限所致,往往會有上下數十年左右的誤差,但時間框架歸入商末周初是確定無疑的,并且,三星堆多座祭祀坑的埋藏年代是一致的。
不過,祭祀坑的埋葬年代,并不代表三星堆文化和器物的鑄造年代也是在殷商晚期。事實上,成都平原的考古學文化脈絡十分清晰,分別是寶墩文化(相當于新石器時代晚期)、三星堆-金沙文化(相當于夏商時期)、十二橋文化(相當于西周至春秋時期)。

其中,三星堆文化一期的時間上限不超過二里頭文化二期(夏文化),這是因為三星堆文化早期遺存中出土了二里頭二期典型酒器—陶盉,陶盉在中原地區從新石器時代到二里頭文化時期有著清晰的演變脈絡,而在成都平原卻是突然出現的,所以,陶盉必然是從中原傳播到成都平原的。
據此,考古工作者才斷定了三星堆文化的時間框架在二里頭文化二期(即公元前1680年—公元前1610年)至西周初年。
換言之,在三星堆人將大量金、銅、象牙埋入器物坑之前,三星堆文明已經存在了近500年,與商王朝存續時長高度吻合。

其次,不論是6月14日成功提取出坑的龜背形網格狀器,還是此前已經大量出土的象牙、金器以及各類造型詭譎的青銅器物,在同期的中原地區都極為罕見,據此,有不少人認為三星堆文化是「西來戶」甚至是外星人創造的。
其實這是對三星堆文化的誤解。著名考古專家許宏教授曾說過:「大家看三星堆某些青銅器的造型感到怪異,那是由于我們的視野狹窄……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什麼發現超出了我們既有的認知范疇。」
事實上,三星堆文化出土的陶器,在新石器時代晚期的成都寶墩文化中均能找到出處,而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青銅器經鉛同位素比值測定,發現所用銅礦與與江西新干大洋洲商代大墓青銅器具有十分明顯的淵源,與長江中下游的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古冶礦礦源一致,特別是出土的青銅尊、罍都是殷商典型器物。

至于三星堆發現的大量在中原地區罕見的金器,則是因為蜀地地處「蜀身毒道」的外貿前言,受外來文化影響所致。類似的情況在我國并不鮮見,比如漢文帝母親薄太后墓中就發現了大量中原罕見的金器,帶有明顯的草原風格,原因就是漢文帝母子曾長期生活在與草原接壤的代國。
三星堆8個器物坑的出土文物基本為破碎殘損狀態,很多器物在掩埋前,還經受過了擊打和焚燒。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迷之操作呢?有人推測三星堆8個器物坑是三星堆被滅國后「入侵」者故意破壞的產物,并非三星堆人的祭祀行為。

不過,這一推測并不符合考古發現的實際。三星堆8個器物坑象牙層和青銅器層排列呈現一定規律,并非是破壞后的隨意丟棄掩埋。何況,三星堆遺址中沒有發現暴力和軍事戰爭痕跡。
實際上,三星堆人對于這些國寶器物的處理方式,同樣沒有超出已有的認知范疇,《爾雅·釋天》曾有記載:「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瘞埋,……祭風曰磔」,無論是燒、砸還是掩埋,都符合當時的祭祀儀式。
不過,如果我們從巨觀的角度去觀察三星堆,就會發現幾個詭異的巧合:

第一個巧合:上文已述,三星堆祭祀坑埋藏年代一致,測年范圍在公元前1131年—公元前1012年,這個時間框架恰恰是商朝滅亡時間。
或許有朋友會問,商朝滅亡時間不是在公元前1046年嗎,怎麼會跟三星堆祭祀坑埋藏年代高度吻合?
其實,夏商周斷代工程報告中就明確提到,兩千多年來中外學者對武王克商年的結論共有44種,大體分為長年、中年、短年三類,分別是:公元前1127年—前1070年,公元前1070年—前1030年,公元前1030年—前1018年。而斷代工程專家組之所以把公元前1046年定為武王克商年,是因為這個年份是符合條件最多的一種,因而定為首選之年。

但如果我們把三星堆祭祀坑埋葬時間區間(前1131年—前1012年)和商朝滅亡時間(前1127—前1018年)年區間看做兩條正態曲線的話,會驚奇的發現兩者高度一致。
第二個巧合:在三星堆文化分布區內,除了已經發現的三星堆祭祀坑外,其他地點極少發現青銅器,這也就意味著三星堆人是在商朝滅亡這個時間節點上,將歷年來積累的所有國寶財富都埋入了地下。

如果當時的蜀地存在濃郁的祭祀習俗的話,那麼三星堆人在文明存續的500年時間里都沒有舉行祭祀,為何卻恰恰在殷商滅亡這個時間節點上,舉行如此大規模的祭祀活動,并一次性將象牙、青銅器、權杖全部打碎焚燒掩埋?
第三個巧合:成都平原經歷了寶墩文化(相當于新石器時代晚期)、三星堆-金沙文化(相當于夏商時期)、十二橋文化(相當于西周至春秋時期)的發展階段,其中三星堆之前的寶墩文化和之后的十二橋文化時期,成都平原都分布著星羅棋布的城邑和聚落,唯獨三星堆文化時期,成都平原沒有看到二級、三級的多層次聚落。

不僅如此,在三星堆文化之后,成都平原的祭祀性遺存全部消失,甚至連三星堆人的太陽崇拜信仰都未傳承下來。三星堆文化猶如一個楔子一樣,插在了成都平原的兩大考古學文化之間,打亂了原本的發展脈絡。
早在上世紀90年代,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研究室主任杜金鵬教授就大膽設想「三星堆二期文化很可能是在夏末商初時,由遷入成都地區的夏遺民,與當地土著居民相結合所創造的一種新型文化遺存。」

1993年出版的《三星堆文化》一書也認為,「三星堆文化分為四期,其中第一期文化的新石器時代晚期先民為四川盆地內的土著居民。」而考古發現也顯示,正是在三星堆文化二期時,二里頭文化(夏文化)因素出現在了成都平原。
此后,隨著考古發掘的深入,三星堆出土文化愈發證實了上述猜想。
三星堆出土了夏文化的典型器物—牙璋,不僅數量眾多,而且在形制上還有改進和發展,出現了銅牙璋和牙璋形金箔。要知道,在夏朝滅亡后,牙璋都進入了衰落期,在整個商文化圈內,牙璋都被改造成了其他器物使用,唯獨在三星堆,牙璋成為了祭祀重器,與商文化圈以鼎為重器的做法截然不同。

根據對三星堆出土青銅人像的大數據統計發現,祭祀坑中出土人像由辮發和笄發兩個社群組成,二者比例為8:2,即辮發者占大多數。但在所有表現宗教儀式場所的組合銅像中,卻全都是笄發。
這說明,笄發者雖然是少數群體,但卻壟斷著宗教祭祀領域,在青銅器象征國力和財富的時代,笄發者壟斷了三星堆幾乎全部的上層資源,故而可以從容地將如此大規模的青銅器、金器、玉石器、象牙、海貝等貴重國寶用于宗教活動,甚至連象征世俗權力的權杖都能被埋入地下。

這一發現,也佐證了三星堆文化是由外來群體和本地土著群體共同創造的猜想,而這個外來群體,正是被商朝驅趕的夏人。
殷墟甲骨文中,屢屢出現「伐蜀」、「至蜀」等字樣,雖然甲骨文中關于「蜀」字有20多種寫法,但共通的地方是都有一個「目」字,描繪的恰恰是三星堆獨具特色的縱目形象。

在武王伐紂時,「蜀」還加入了伐紂聯盟。就在商朝滅亡后,三星堆人(蜀人)不僅舉行了盛大的祭祀儀式,埋掉了幾乎所有的國寶重器,而且還舉族遷徙。
雖然我們不知道在商朝滅亡后,三星堆人內部究竟發生了什麼,又為何遷徙,但也恰恰是在商朝滅亡以后,三星堆濃郁的祭祀文化突然消失,隨后在西周初年出現的弓魚國,雖然出土了跟三星堆金杖上的「魚鳧形」紋飾相同的器物,但此時的弓魚國早已演變成了徹底的世俗權力方國。

顯然,由夏遺民和蜀地居民共同建立的三星堆文明,在完成了伐紂大業后,掌管神權的笄發群體退出了統治階層,統治社會的不再是神權,而是世俗的政治和軍事勢力。在祭祀坑中埋葬掉幾乎所有的國寶重器,似乎是笄發群體在向祖先進行最終告慰。